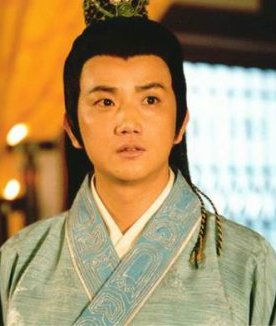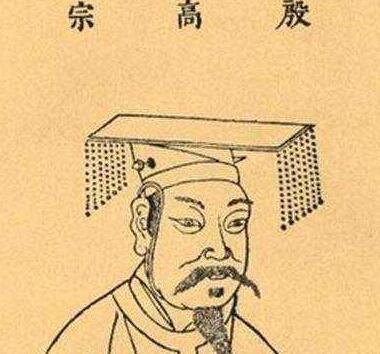由此可见,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,忽必烈就有“大有为于天下”的抱负,在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。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很有兴趣,非常的神往,这就象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,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样,所以,当时的忽必烈就已经延聘了不少的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,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,这些许多汉族的幕僚中间,有一个当时叫做“子聪”的和尚,他就是后来主持营建北京城、改国号、制定朝仪的刘秉忠。
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,由刘秉忠领衔,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,呈文说:“元正、朝会、圣节、诏赦及百官宣敕,具公服迎拜行礼。”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,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,忽必烈非常高兴,批准了他们的方案,正式建国号为“大元”。为此,朝廷下了一道诏书,公告天下。
在古代,朝廷的诏书也都是很好的文章,因为写诏书的人都是当时文人的冠冕,如果没有一流的文章手段,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来为自己草诏,所以,这些诏书也都可当作好文章来一读,这类文章一般来说,都非常大气、庄严,又有雄辩的说理,又有华丽的辞藻,甚至还有平易近人的态度,让天下的人听起来能够心服口服。不信的话可以试读一下这分诏书,诏曰:
诞膺景命,奄四海以宅尊;必有美名,绍百王而继统。肇从隆古,匪独我家。且唐之为言荡也,尧以之而著称;虞之为言乐也,舜因之而作号。驯至禹兴而汤造,互名夏大以殷中。世降以还,事殊非古。虽乘时而有国,不以义而制称。为秦为汉者,著从初起之地名;曰隋曰唐者,因即所封之爵邑。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,要一时经制之权宜,概以至公,不无少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