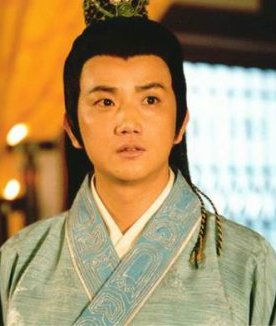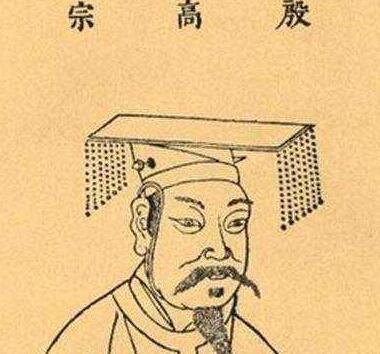诸葛亮之所以在投靠刘备前期并未受重用,也在常理之中。刘备戎马半生,而诸葛亮初出茅庐,在没有足够的军功之前,一纸《隆中对》也很难让他立刻成为谋主;反而是刘备“与亮情好日密”,致使军中元老关羽、张飞不悦,三人的矛盾也就此埋下伏笔。赤壁之战中,诸葛亮并未直接参与军政,其功在于出使孙权建立孙刘联盟,这是诸葛亮威望之始,却又加深了关羽之妒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对此评价到:“昭烈之败于长坂……羽不能有功,而功出于亮。刘珂曰:‘朝廷养兵三十年,而大功出于一儒生。’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(鲁)肃,因之忌吴,而葛、鲁之成谋,遂为之来裂而不可复收。”
赤壁之战后,刘备坐收荆州四郡,诸葛亮的职责依然只是“督零陵、桂阳、长沙三郡,调其赋税,以充军实”,也即是内政。如果说《隆中对》与建立孙刘联盟所展现的分别是诸葛亮的战略眼光与外交手段,诸葛亮从事内政也是情有可原,那之后刘备对庞统与法正的态度就令人沉思了。
刘备平益州,选择让庞统随行入蜀,后庞统死于雒县之战后才宣诸葛亮随行;之后刘备执意东征,诸葛亮又叹曰:“法孝直若在,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;就复东行,必不倾危矣。”由此可见刘备心中,对庞统、法正的任用与器重,至少是不亚于诸葛亮的,尤其是睚眦必报的法正,诸葛亮甚至因为其受刘备“雅爱”而对其无可奈何,以至于发出了“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”的感叹。个中委曲,民国时期历史学家田余庆曾有精辟论述:“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,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。”
也就是说,刘备之发迹,只取诸葛亮之《隆中对》,却并未真正重用其人;而即使在外交内政方面,诸葛亮也一直受到关羽的掣肘,刘备的“鱼水之喻”不能不说是有些水分。然而,庞统、法正均早夭,刘备帐下三大谋士仅存诸葛亮一人。刘备临终之时关羽、张飞等蜀汉元老均已亡故,此时“召亮于成都,嘱以后事”从主观上未必是违心之举,但从客观上却是唯一的选择。